客串中國人
記得柏楊先生在其名作《醜陋的中國人》中講到,『我們的醜陋,來自於我們不知道我們醜陋』。在接受出生的宿命之後,去過香港之前,中國人的文明社會僅存在於我的臆想和新聞報導中。殖民是一種罪惡,但帶來的文明孰好孰壞難以定論。正在我庸人自擾之時,一名香港衛生署的工作人員將我從入境的人流中請了出來。
被告知應多飲水來防止中暑之後,我輕鬆地隱入人流進入香港。嘴角邊的一絲得意,表達了我第一次與政府工作人員暢快交流的滿意。搭乘列車前往港島之前,我像很多港人一樣,在路邊的7-Eleven買了飲料和新鮮的《蘋果日報》。『九七』之後,香港媒體獻媚似地『自我審查』。無國界記者每年的傳媒自由度排位中香港逐年下滑,更是跌到了大多數歐洲國家之後。以我六月五日親見,願意頭條報導『六四二十週年,維園十五萬人祭』的本地報紙僅三家。其中《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是本港最權威的英文報,主要面向受高等教育的一代及外籍人士;而大俠金庸主辦的文人報紙《明報》,雖連查老先生都話大不如前,但仍會矚目於這一本港婦孺皆知的大件事;以八卦自由蜚聲國際的《蘋果日報》,誇張地以支聯會估計的『二十萬人』來作報導噱頭。六月四日當天,大街小巷衆多港人翻閱的《蘋果日報》,有多個主要版面為各民主團體整版刊登『平反六四』、『正視歷史』、『今晚維園見』的巨幅廣告。相信這也積極地促進了當晚十多萬人前往的盛况。
每次我說要去香港買書,很多朋友都會覺著奇怪。首先,香港根本沒有一家像深圳中心书城那樣規模的書店,有足夠多的庫存供選購。本港大多數書店都窩在某條小道某棟舊樓的角落,而且通常不大,庫存的確有限;另外,由於香港人工和物價高,港版書售價通常都在大陸書的兩到三倍以上。理論上講香港買書的確是很不劃算的。所以大多數人認爲像我一類赴港購書之輩不過是獵奇禁書而已。當然,竪排及繁體中文閱讀的不暢也是很多人拒絕的潛在原因之一。其實閱讀過一些原版古籍的話,自然不會以此為礙。問題不過是文明進程中文化的丟失而已。走進灣仔的某間書店,我不得不承認『痲雀雖小,五髒俱全』的道理。我買書讀書,也漸漸傾於『精貴於多』。我常常在一棟酒店式的新華書店裏逛一個下午找不到一本想帶走的書。以前聽到一則老故事說一個大陸游客第一次到香港,然後在街頭某間小店把他這輩子想聽的唱片都找齊了。我不好音樂,香港的小書局能給我類似的快感,有一種人文關懷在這裏。每個書類下都有港版、台版、大陸版甚至英版、美版的圖書,無疑代表著國際中文圖書市場的縮影。包羅萬象中不排除有大陸所謂的禁書,但更多是大陸市場難以見到的好書。的確由於價格不菲,我買不了多少書。但能入手一兩本心儀的書對一個讀書人來說,喜悅難以言表。
英文書籍在本港市場上也是非常豐富。不管是『葉一堂』(Page One)還是其牠小店,我總是能發現許多來自世界各地的圖書精品。大陸政府對圖書進口的管制無疑使更多優秀的書籍難以走近民衆。而中西文化交融的香港,東方傳統和西方文明在一種動態平衡中促進這個社會的不斷進步。
後來我去了香港中央圖書館。進去後猛然發現,我從小心目中夢想圖書館的樣子,原來就是這個樣子。陽光下圖書館泛黃的外牆使這堵舊樓遠遠遜色於周遭的商場寫字樓或民宅。我總是不明白,爲何清華北大老想拆樓重建,一定要外表個個如鳥巢纔能表示藝術效果?我倒是認爲歷史的痕跡更能體現知識的沉澱。中央圖書館內完備的各類設施及布局管理令人印象深刻,值得很多現代圖書館學習。館內工作人員和讀者們都讓我感覺到了現代文明。另外我也覺得,政府真地給願意增長知識的人提供了一處絕佳的環境。我在這裏又找到了一些久仰大名卻沒機會閱覽的書刊,比如著名的現代哲學雜誌《今日哲學》(Philosophy No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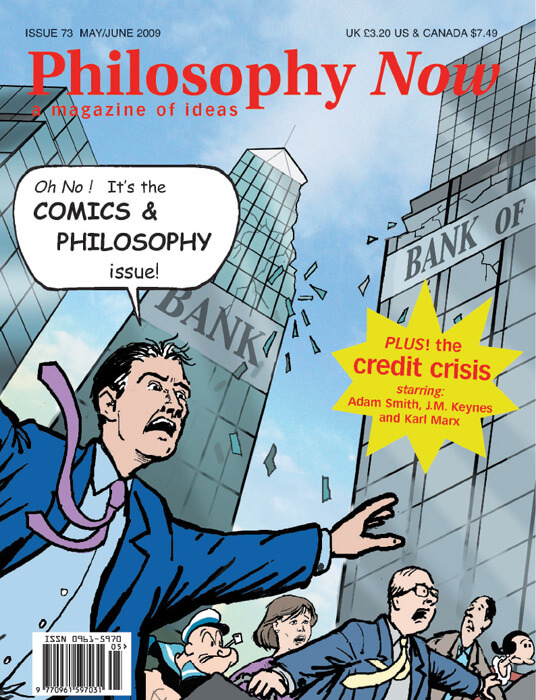
現在回到我入境香港之前的思考,『殖民是一種罪惡,但帶來的文明孰好孰壞』?廿年前的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十四世達賴喇嘛丹增嘉措先生常批評中國政府對西藏文化的嚴重破壞。我就此事參照了港英政府殖民香港的類似情况,發現問題的最大不同點在於,英政府畢竟給予了香港人民更多更廣的自由和民主機會,所以文化得以傳承而不是斷裂。百年來東西文化衝突在香港並不少見,最終能在文明進程中融合,實屬不易,更值得西藏問題借鑒。甚至在很多方面,優秀的東方傳統在香港文明化進程中,能比盲目文明化的大陸保留得更好,比如民俗,比如歷史,比如禮儀。這也是香港文化的迷人之處。
香港絕非完美。人口爆炸,經濟社會問題叢生。但有一點可貴的就是,港人可以看到問題,提出問題,解决問題。這是一個自由社會的精髓。在銅鑼灣一間不足千呎的二樓書店,我撞見一名港人在午餐時間抽空上來預訂下週再版的近日超暢銷書《改革歷程》。看來我是暫時沒機會搶到這樣一本趙紫陽老先生生前錄音的藍本了。逛店期間,我還聽到店內兩名店員亦或店主正談及今晚要早些收工去維園呢。
八九年之後每年六月四日,香港維多利亞公園是全世界最大型公開紀念那場民主運動的地方。因爲最理想的紀念場所北京天安門廣場在平反之前絕不會有任何機會開放。香港市民多年來的堅持,更是不斷感染世界各地的友人前來參與。鄧小平爺爺當年也許真地說過『殺二十萬,保二十年穩定』。時間過得真快,已經二十年了。鄧爺爺早已不在。看到報紙上當年學生領袖王丹、柴玲、吾爾開希現今一張張蒼老的臉,人們能不感慨麼?香港市民支持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主席司徒華就這樣在維園台上吼了二十年。如二戰期間協助藝術家逃離希特勒歐洲的美國民間團體一樣,岑建勛一幫人自發營救民運領袖的『黃雀行動』也漸漸浮出水面。人人也都希翼如韓國『光州事件』十六年後平反一般平反六四。在二十週年的特別時刻,港大民調顯示支持平反六四的本港受訪者昇達百分之六十一的新高。經濟不振的香江,支聯會的聲音的確微弱了許多,但諸如港大前學生會主席陳某或特首『煲呔曾』的不負責言論仍會遭人唾駡。『小馬哥』就任中華民國總統以來,身份地位令其調軟,但六四二十週年當天的感言也算底線。晚七時多,我在中央圖書館內正沉迷於某本René Descartes的論著時,隱約聽到館外《男兒當自強》的音樂,心想糟了,便輕輕將書放回原架,匆匆下樓前往街對面的維多利亞公園足球場。
下午我就頂著烈日來探過場地,也旁聽了程翔和司徒華等人的講座。現場黃昏時分天氣狀况良好,看來連老天爺也願意行這個方便給大家。可容八萬人的足球場連通道上都聚滿了人,卻沒有擁擠和吵鬧。支聯會隨後宣布已獲批首次開放旁邊的籃球場供集會,並建議新入場的民衆坐在維園草地上。幾百吋的大螢幕還是看不到?沒關係。趙紫陽的錄音聽不清楚?沒關係。熊焱的講話不够振奮?沒關係!我和大家一樣,在支聯會的義工處領了蠟燭和紙罩,找一處滿意的位置默默坐下。當我開始考慮沒帶打火機如何燃起這燭光時,發現在場大部分人都差不多這樣。一切盡在不言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第一次現場感受了數萬人被同一個理想點燃的偉大力量。
向來行事低調的香港名作家李碧華女士當年有一本《天安門舊魄新魂》結集她的感言。我在維園中間走動的時候就想,現場燭光中肯定少不了她,還有梁文道,陶傑一圈文化名流的身影。李女士在隨後兩天《蘋果日報》上她的『礦泉水』專欄中撰文《在這天吃素》,提及了今年維園燭光的空前。文中還講到某年集會散後她在銅鑼灣夜宵,『遇到一些年輕的大陸遊客,選擇六月初自由行,特地在自由的香港,向祖國無辜死難者致祭』。過港來真正『自由行』一把的大陸遊客肯定不少,我從當天現場支聯會透明捐款箱裏一些夾雜在花花綠綠港幣中的紅色毛氏頭像鈔票可窺見一斑。
除『天安門母親』、『我要回家』和一些其牠香港民間團體的募捐外,我沿途也收到了一些派發的資料,如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城市大學等七大聯校學生會合編的《我們二十——國家走道哪裡》,中國人權論壇出版的特刊《直面『六四』國殤》,還有去年聲勢浩大的《零八憲章》宣傳。作爲主要發起人的香港支聯會在五月三十日的遊行合六月四日的維園燭光集會作的都還不錯,整個集會在義工與大衆的配合下井井有序,非常文明地進行中。現場我也見到了不少歐美人士,以及各類媒體記者前來采訪報導。新聞自由,的確讓更多真實能被廣泛地傳播。為賣劇集到大陸而淪落到自我審查的TVB無綫電視被港人戲稱為『CCTVB』,更別提一蹶不振且被大陸商人註資多年的亞視了。周星馳九一年的喜劇電影《整蠱專家》中有一段對白,是他吃了謊言豆沙包後說的:『袁木好誠實,李鵬是偉大領袖!』。黃霑叔八九年以聖誕樂曲配以政治諷刺填詞出專輯《香港X’mas》來發泄了不滿。梅姑生前對支持八九民運一直堅持不懈的積極主動更令人欽佩。可是回歸之後,娛樂圈誰不想在大陸市場分多一盃羹?所以成龍大哥之類的情况纔會越來越多。不排除今年十餘萬維園燭光中有多少社會名流,也有當年跑馬地《民主歌聲獻中華》一眾歌星的參與祈禱。但誰還要站出來麼?香港的民主運動本身也經歷多年滄桑。十年前許鞍華導演的一部低票房作品《千言萬語》重塑了香港民運的真實,還是讓不少港人感嘆,所以獲獎是有道理的。影片結尾的鏡頭正是紀念六四十週年維園燭光的寫照。眨眼已是六四二十週年,人們最擔心的還是,有的東西難以在剛長大成人的『八零後』、『九零後』身上傳承。沒有吃謊言豆沙包的我們,能不能講出事實的真相?
香港中學生和大學生通常都參加一些義工組織或民間團體來豐富課餘生活,而一些中堅的自由媒體仍能讓新生代不斷獲取更接近真實的資訊。相比之下,大陸學生一直受壓於高考,且政府限制多方面消息傳播,使得很多評價難以更客觀了。所以蠻多受主流媒體影響到的大陸年輕人認爲『經濟繁榮,社會穩定』的表像可以掩蓋『六四』那一筆。聽不到異見的觀點,從而無法引發更多思考,這就是問題所在。去年溫家寶總理在紐約接受CNN電視台專訪時,主持人展示了那張溫當年陪同趙紫陽在天安門探望絕食學生的經典照片,溫總嘴角一陣微顫。這樣的新聞價值是沒法在中國中央電視台每晚七點强制全國人民收看數十年得到一個破世界記錄收視人數的新聞聯播節目得到的。從當年上海《世界經濟導報》被市委書記江澤民查辦開始,到最近六四二十週年期間大陸互聯網全面禁止網民發表任何言論,更多的內容都是艱難地在人們口中傳播。更多當年的消息,我們依靠的還是收集境外媒體的的隻言片語。美國PBS電視台九五年出品的《天安門》(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以及零六年出品的《坦克人》(The Tankman)兩部記錄片都值得一看。中國境外出版的八九民運書刊更是不勝枚舉,衆多前線記者合著的經典《人民不會忘記》已經再版。老牌的政論刊物《開放》雜誌也是非常不錯。這些東西都能在香港找到。
我很願意闡明我自己的一些觀點。『六四事件』或稱『天安門大屠殺』是『八九民運』的一個重要部分,但漸漸變成了其標志符號。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清晨的天安門廣場由於軍隊清場而異常混亂,但如PBS、BBC等外媒記者所目擊,廣場本身死傷並不嚴重,與軍隊衝突也不明顯。實際上,更多的傷亡發生在天安門廣場附近和京城各處。比如世界聞名的『坦克人』王維林先生便是出現在長安街上。具體傷亡我認爲可以參考當年《紐約時報》記者Nicholas Kristof嚴謹的調查報告。之外,我也承認當年的鎮壓是換來了這二十年的發展和穩定,可是人民仍然沒有民主和自由。政府可以說那玩意兒是西方帝國主義的把戲我們不需要,但作爲現代文明的一部份,這些都是人們真正需要的。趙紫陽當年推進的全面改革二十年後的效果不見得會比現在差。在如今經濟強勢的社會中,中國人的文化繼承在大陸的確是非常糟,比香港、台灣完全不能並論。例證大家也都目見耳聞。所以我一直持有一種身份認同的觀點:只有生活在中國境外,纔能感受到自己是一個真正的中國人。因爲惟有這般,我們便能聽到我們的醜陋,看到我們的醜陋,還願意去剝掉我們的醜陋。

己丑黃牛年五月十五 書於錦官城南